事实上,我们很难回忆起自己的初心。
去年年底和Liz谈过一次。那是一段很尴尬的谈话,关于理想、未来和Kicity*。少数熟悉这一博客所有发展历程的读者可以知道,初期的Kicity*除了配色和现在一样,基本上没有什么共同点。这也是我在去年计划恢复历史数据时所感到的困惑。有时候你会给这种健忘寻找一种理由,例如成长,例如外部形势的改变(是的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理由),甚至例如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看起来一切事情变得冠冕堂皇,消费主义、电影和追剧狂热、夜店文化、各种流派的权利主义、对于房子和投资的无休止的讨论。所有人都在迎合一种所谓“酷”的标准,这种标准随着阶级、教育经历和工作城市有所区别,但终究在同一代形成了一些令人惊讶的共识。这很像八、九十年代的日本,不过如果将其归结为泡沫经济共有的特点,恐怕是在这外表已然华丽的冠冕上徒增一笔而已。自那场对话至今我们都再也没有交流。我很开心她还记得那些东西,我也收藏了一些。
研究生申请前和面试官Richard聊了一次。他是一个中国通,在华有很多年的企业咨询经历。我们谈了行业环境、市场氛围和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诸多瓶颈。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市场,复杂到Liz无法通过本国的网络来访问这一博客,也复杂到我们在热爱技术的同时还需要和很多匪夷所思的名号来打交道。很多人因为这些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乐于谈论的对象,也有很多人在此之后一文不名。看起来我们有能力选择打开或是不打开装有蛇的笼子,但可能这也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而已。Richard说我可以利用自己的中国背景,着重自己在中国市场上的理解和经验。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背景会是加分项,尤其是在这一申请季受到一些奇怪的待遇之后。
面试的时候问到了在幼年时期的不如意的事情。我提到了户口,提到了我三所小学两所高中的转学史。出于一些顾虑,这在简历里没有体现,还好我的面试官是一个同样理解中国的人。但这也使我回想起幼年时代以至今天困扰我最大的问题。
我是谁?
我的前六年成长在黑龙江,这是家乡,没问题。接着我转学去了山东,以黑龙江学生的名义,除了受到山东教师对外地教学能力天然的不信任外也没问题,我证明了自己。再之后我转学到了北京,问题开始有些棘手了,除了各种毕业证书的籍贯自此都变成了山东以外,我还需要证明很多别的东西,例如北京人骄傲的英语,或者是强势的文化。再之后我去了河北,河北人痛恨北京,因为北京过于占用了他们的资源,而我又和北京扯上了关系。阔别九年之后我回到了黑龙江,好在老乡们在第二节体育课就接纳了我,这也是我非常感激的一点。最后我以黑龙江人的名义考进(回?)了北京,有一次一个新疆女生说我的京片子是“东北话重”,我很难理解;而我又重建了小学和初中的社交圈,有时候这也会令他们的同学费解。
我失去了老家。我再也没回到黑龙江的学校,抚摸那一块刻有我名字的石碑。
我试着去找回和之前同学的一些联络。之前和我关系非常好的几个同学。王去江南大学读了日语,之后还偶尔和我诉苦日本的官僚主义。陈复读了一年,进了我们省的商学院,毕业即失业。前年陈来了一次北京,我带他逛了逛鸟巢,看了看北京知名的“大裤衩”,然后请他吃了北京菜和日本料理。我能感受到他的不适应。在日本料理店里他每句话都说这“小日本”怎么的怎么的,我也只能跟着他一块说“小日本”怎么的怎么的。后来他去了P2P金融推销随时会跑路的产品,再后来他辞职来北京找了一份两千五百块的工作,即便他从寄住在燕郊的亲戚家往返苏州街每天要花上五十六块钱。他这次变得平和了许多,我也熟练地避开一些话题,和他一起声讨北京过高的房价。
我感觉和家乡人有了一丝联系,也进一步确认了我目前处在的阶级。这是对于“我是谁”这一终极话题的重大理论进步。
即便我还是回到了去年年底的那一场困惑。
2017年3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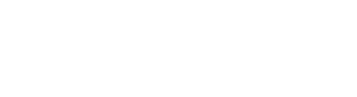
这也是我大晚上更新LinkedIn页面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