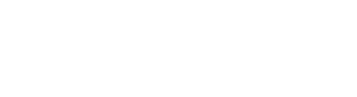当我碰上它的一瞬间,我就知道,它就是真理。
或者还没碰上的时候。
它从窗外冲了进来,合乎道理的,就直接闯了进来。没有手脚,手脚会挂住窗框,它摧毁了一部分墙壁。我没注意,墙壁可能没有破碎,和窗户一起,和空气一起,像是钢化玻璃一样,碎裂了,但是又没有渣滓。
一层一层的,连续的,它可能是黑色的。没有头颅。
可能是巨大的蚯蚓,它是真理。当时我躺在床上,半躺着,靠着墙边的枕头,米黄色的,和蓝色的墙纸质感差不多的,我唯一能够感受到的温暖,或者说我目前能抄起来的唯一能对抗真理的工具。手头上大概还有别的,手头,手是什么呢。
我一直期待着真理,真理告诉我,我叫叶公。它实在是太庞大了,等一下,庞大,我能感受到它的形状,那它还没能完全占领我。它是巨大的,我试图描述它,是我小时候经常做梦的那种,在看完一九九七年第一部三维动画片之后的梦,我和它在下象棋,模型粗糙,对,不能沉迷在多边形的细分计算中,我活了过来,对,象棋,中国象棋,米黄色的棋子,和蓝色的棋盘。
每次都一样的残局,记不清楚了,没法描述,没法描述,已经没有几个棋子了,可以移动的步骤七只手大概就能数出来,都是一样的。每走一步,它都告诉我,这步棋对我来说太过沉重。
我已经死了。
或者说,没有任何移动空间了。
正如此时。我的鼻尖触碰着它,眼前勉强留出了一点对焦距离,模糊的,为什么我的眼睛是2.0的,我看不清近处的它,它的内在闪烁着,是米黄色的,和蓝色的。蓝色的大概是血液。
眼前有很多人,漂浮着,相对方向一致的,这样比较节省空间,能容下更多人。我能看见月河小姐的八卦耳钉,转啊转啊,是真理的蜂群中唯一反方向运动的。但是我看不见月河小姐,我谁都看不见,他们花花绿绿的,混沌的,轮流着闪光,总之都差不多。
那么我能确定,因为真理里面有他们,如果真理是他们叠加起来的,真理是黑色的。
这是第二个枕头了。我需要一个白色的枕头,来对抗黑色的真理。第一个呢?
白色的,白色的是什么呢?是地狱。对,是地狱,是地狱。稍大一点的时候,我也以为地狱里会有火焰啊油锅啊这种比较好看的东西,至少奈良的地狱展是这么画的。 骗小孩的。在油锅里的那阵,我全靠着数油锅里的泡泡打发时间。小鬼看我太无聊,就问要不然你去真正的地狱待会吧,要不然我交不了差。我说行,小鬼长什么样不重要,大概挺好看的。
然后地狱就是纯白色的,啥都没有,没有东西可以数。我知道了地狱是白色的。地狱和真理是反义词。
我就这么醒了。我也不知道第二个枕头哪里去了。
于是我今天晚上没有枕头。
也没有了真理。
心心念念的。
至少我现在期望着另一个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