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6年的夏天,我坐在教室的倒数第一排,风扇转啊转的。讲台上在讲南美解放者的故事,历史老师是学校返聘回来的前校长,口音很重,总把伊达尔戈念成“一大二哥”,我很喜欢他的课,连大学领快递的时候也用他当作假名,买男装的时候就用“枚”当名字,女装的话就用“美”。
对于伊达尔哥的故事,我已经不怎么记得了。倒是偶尔会回忆起来午餐的压缩饼干,就是那个忍不住吃两块就会撑一天的,老板竟然被猴子谋杀的冠生园;图书馆的《炎黄春秋》,如果不上台面的话大多数时候是《电脑报》;还有一块回家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回家的路很短,路面不太平,树木的根系把地砖撬得左歪又拧,情侣的勾肩搭背不太可能,只能一跳一跳地,几个人在前几个人在后的样子。有时候一个人走在后面,听到前面的大家讨论有趣的事情,快走几步想走到前面,每次他看到了,就会给我让一个空当出来。
他和我是在剑道社的见习上认识的。每学年开学的时候,各个社团都会抽出一周时间来公开表演,吸引新人。他那次观摩时候就坐在我边上,看见我手上抱着一本盖馆藏章的《宫本武藏》,就稍微聊了一下日本历史。他长得就很像剑戟片主角,两腮上有褐毛,最喜欢的电影就是《七武士》,而我更喜欢《影武者》一些。剑道的装备对于我来说太贵了。
在通学路上碰到几次,久而久之,我们熟络起来了,有时候也会互相带上各自的好友。比如他的初中同学,一个满口脏话的大汉,我不是很喜欢那个人的话题,不过我和这个人的交情竟然也持续了很久,在池袋的东口,从洛杉矶,直到密克罗尼西亚群岛,这个人从街头顽主变成了一个体面的生物学家,这是很久以后的历史了。还有一个女孩子,和我一样也是班里的转学生,摄人心魄的好看,但是名字很土气,就还不如我的“美”字,她就住在我正楼上,有时候我会在楼梯上给她讲题,然后再跑到楼下煮自己的饭。我想上去和她一起吃饭来着,她和她奶奶住一块,我一个人住,我准备我们的孩子叫迪皮卡。
总之,即便路上有些许的快乐,那段时间的基调也是昏暗的。下课的时候,有时候也在上课的时候,我写了很多很多本日记,一些诅咒或者形而上学的东西。我听流行摇滚,电子音乐和所有被小众不齿的东西,说实话我喜欢它们之中的大多数,唱歌很好听,我也从和他们的接触中得到些许安心。相比之下,和他说的话就少很多,我们还一块打日本麻将,在网上和大牌能蹦出凤凰的那种。我不赢不输,他也不赢不输。
自从那个女孩子入学,我们几个人走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多了。有时候会讲起互相的事情,或者理想什么的,可惜自从在卡塔拉海滩趟过一回之后,那些理想都已经忘个差不多了。有时候他也会撮合我和楼上妹子,可惜到毕业的时候我也没什么进展。到底是他不会撮合,还是他也有点喜欢这个女孩子,当时我觉得是前者,很多年后我觉得是后者比较多。我试着在人人网搜那个女生的名字,大概一年总会有那么几个混账的晚上,但是都一无所获。大学我们竟然也在一个学校,同一楼层的寝室。有时候半夜站在路灯底下,和他喝7-11的朝日生啤。聊起高中时的女孩子时,偶尔他还会揶揄我。当然,对于啤酒的赞助人,这点程度的揶揄我也是能接受的。大学他还在剑道社。毕业前我们一块看着满月,说起在一块芝加哥的好日子,说冬天的大雪把车位都埋起来了;说他要结婚了,洋子怀了他的孩子。
毕业后他住得离学校很近,我却在南城稍微有点距离的远郊,有时候提前一周约出来一块喝酒,说到底这个有时候也仅仅有一次或是两次而已。那家酒馆的啤酒有股香蕉味,可能也有大麻味,可能大麻味是来自周围环境的,也有可能我以为的大麻味就是醉汉的尿骚,我不确定。我们还是聊了近来的日本文学,聊了黑泽明,临走在地铁站,他说他要去解放南美了。
研究生的时候,我和大学同学一块去墨西哥玩。我们准备去墨西哥城、瓜纳华托和坎昆。也准备去韦拉克鲁斯,但是似乎中间的公路不太安全。在墨城我们住的地方就叫Hidalgo,地铁站是一个绅士的标志,我们戏称这站叫“黑大狗”。出站的时候,站口有一些流浪的小孩向我们吹口哨。
我突然想起来,这里原来就是伊达尔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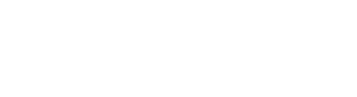
[…] 墨西哥酒店的早餐都很好吃。CDMX住的那家也是,房间很差,但是早餐的蛋比连锁大酒店要棒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