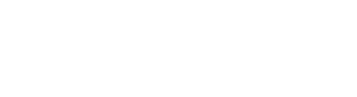“你下次来德里的时候,告诉我一声。”跟其他成功的印度商人看起来一样,Anuj诚恳地直视着我,脸上的须发在白炽灯下泛出光芒,“跟着Lonely Planet 的话,你哪都去不了。”
Anuj 是我信赖的人。虽然作为北方人的他,肤色不如别人那么白净,总是说自己在古尔冈的有过高薪的管理工作,也喜欢在酒后吹嘘自己家族在某个Google Maps 都找不到的土邦英勇抗击英国侵略,他的确是个手腕上绑着很多彩绳的婆罗门,一个和某位看起来明显更婆罗门的教授拥有相同姓氏的的青年男子,以及一个不错的人。他不会在交作业前十五分钟还搞不明白排版,也不会在ins 上连发一年排灯节拍的盛装照片。他很简单,任务给他,按时完成,质量优异。
和他的工作如此愉快,以至于我们经常约在同一个小组,在农学馆里一遍又一遍续展自习室占用时间。伊利诺伊的夏夜非常清爽,在布满着萤火虫和蚊子的小路上,Anuj , 我,美国非裔Harry 和俄罗斯人Pavel 聊了很多政治,其中大多数是美国和中国。每当说起外人略微难以理解的事情,Pavel 总是打圆场,“这个只有我们共产主义国家才懂,” 但大多时候我们互相理解,比如他自己为什么从莫斯科跑到赫尔辛基才拍到一张签证,比如Anuj 为什么放弃他口中的高薪工作来到美国。
大多数假日他们去我的居所。这间公寓看起来还算体面,有明亮的灯、两层门禁、体育台和洗碗机,足以让大多数我愿意邀请过来的外国人发出惊讶的神情。在一个学期过去之后,我也常被邀请去Anuj 的合租房。我们坐在老旧而潮湿的沙发上,喝着他手工的小豆蔻茴香奶茶。我看到他家冰箱里有一点金汤力,如果是我的话倒一点酒可能更不错一点。我们试了试北部和南部的食品,聊了种姓、印巴分治、几次战争、全国居民账户、当时刚刚发生的货币废除事件、或是他们来美国所要的高利贷和工资抽成。他也问了很多道听途说的,真实或者虚假的事情。我们一度哽咽,关于我们的历史和现实。当然,在我告诉他Tata公司生产的车型在我们那边也叫面的、三蹦子和半截子,并以此推导出德里房价十几年后也会大涨的预测时,我以为我们处在一样的社会,不同的年代。
但我不想再陈述一些关于全球化的东西,就像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是的,我们最后终将融入全球化,就像我们出差不会选择Taj 酒店一样。Marriott 和 IHG 给我们高级会员和企业房价,不用踏出酒店一步就能和各种口音的商人谈论业务,门童的问候声和早餐培根都是世界统一的标准。一切都是美元标价,一切都和跨国公司报销手册挂钩。Anuj不会回到印度,和我们不一样,又和绝大多数的印度同学一样。他会工作、看网球赛、去芝加哥城郊的巨大印度教寺庙参拜、在Facebook 上为全世界各种灾难的受害者捐款。他依旧信奉着他所相信的,依旧牵挂着所出身的国家,依旧走着我不熟知的那条道路。我思索着他属于我们之中的哪个年代呢?是老移民、血卡华人、九十年代移民、新千年的穷苦留学生,还是和我们同一断层?我突然不想思考这种问题了。印度和印度人一直在变化着,就像外面的人不理解不同时代华人的断层一样,我们也不能完整描述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
这不是投资德里的好时代,德里的房价已经够高了。但可能德里的房价比我所听说的胡志明地产还低一点,他们又比东京高那么一点。这种比较也是徒然的,它的土地产权和我熟知的城市都不一样,它的富人、穷人、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乌尔都人、庞遮普人,全都和我熟知的不一样。现代印度激进的扩张和我们想想的不一样,房间外窗能看到的贫民窟不一样,电视里在乡村所向披靡的毛派政党也不一样。这不一样,这不一样,请收回这份傲慢,你,和我,或者说我们,现在就是处于同样的时代,这个在日历上被命名为2020或是即将2021的时代,德里即将恢复它被英国人埋在土里的辉煌,或者吸干它的地下水之后迁往他处,或者在一片废墟中走向崩溃,这是德里的道路,和我们的经验没有什么关系。
去年夏天,Anuj突然给我发来一条信息,“我过几天要去广交会,一块出来喝个酒?”
“你丫知道北京到广州比柏林打到莫斯科还远吗?”